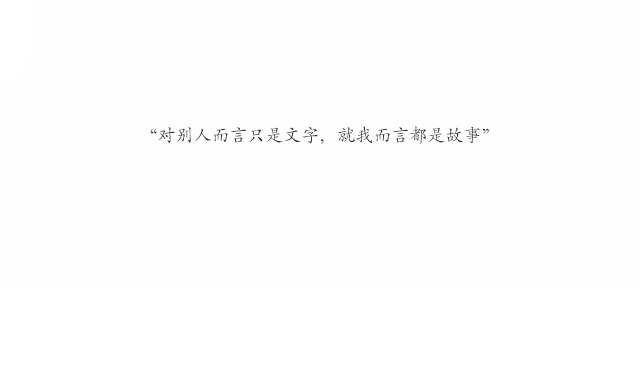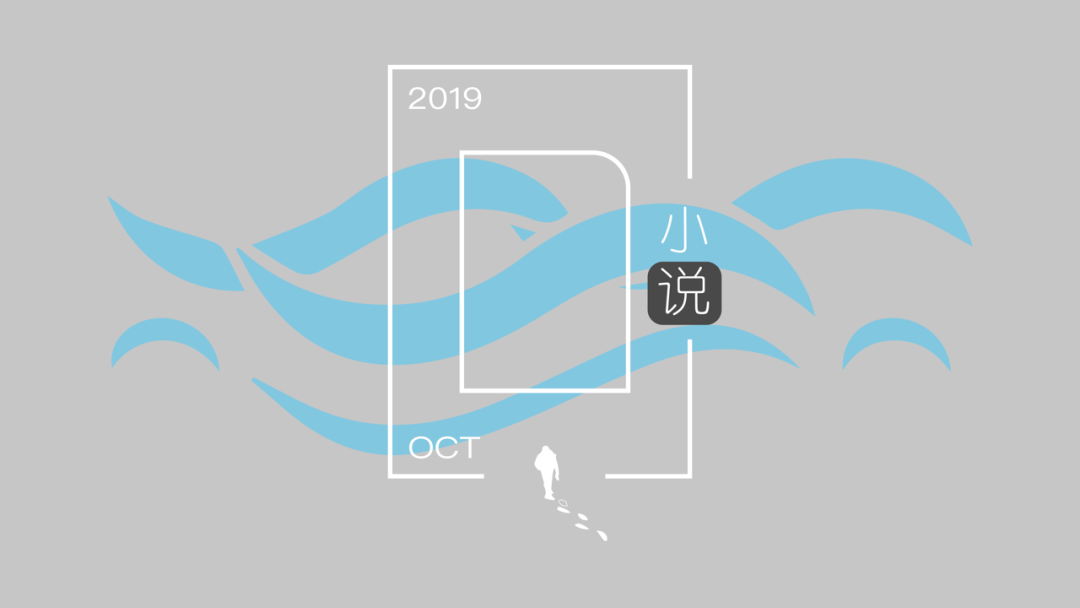
(1)
这是个岛。
四周为海。
我出生在这,据说出生的那天倾盆大雨、大风大浪、波涛汹涌,反正没任何好的兆头。她不为我的话所悲凉,只说我的修辞过于单调平淡。
“此话咋讲?”
“形容雨水就要银河倒泻,形容海浪则沧海横流。”
从小到大她捕捉的点都别于常人,说话会往前平视,从边缘再延至海平线。
眼眸汇入天光,润然宁静。
这位爱看海的姑娘比我大三岁,邻居的,从小就认识,但我从不喊她姐,一次都没有,仅喜欢她最后一个字:纯。
纯生在香椿,暮光垂于子夜,上面还有两位姐姐。出生的当晚万里无云、月色皎洁,据说这吉日降临的人必然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纯出生的那瞬,其父一度想把她赠送友人,一心只想求子,友人已欲上门所取。几次下来其母不舍,毕竟十月怀胎血浓于水,因此赐字为纯,寄望纯如纸、纯如海。
纯的伊始,会有人取其谐音——“蠢姐,蠢姐,大蠢姐。”
起初几分抗拒,后来对恶味的玩笑不介意,因为她不蠢,自上学每年拿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有一回我找她玩,见面后她留意到我的裤裆。
“别胡思乱想,出门前喝水有点急……打湿的。”我解释。
她为此一沉,“尿。”
“尿哪有可能会湿成花洒状?”我辩解。
“风,”她不急不慢,“你撒尿时起风了,风把尿吹成花洒状。”
小岛确实长期起风,风很乱会呼啸,老一辈说是海妖下了诅咒,限期千年,若要提前解咒只能平息大海,减少捕捞。
减少捕捞我们吃什么?
反对者与支持者对半,那回曾有一战,而纯站在支持者方,当时她刚上小学——“珍惜海洋资源,造福子孙后代”,瘦小的身体挤进人群中还越挤越前,声音很奶且突兀。
队伍的口号慢慢变成纯喊前半句,“珍惜海洋资源。”其他人喊“造福子孙后代”,效果很好,纯还被推到最前,晃起小身子从牌坊往巷道迸发,看似要成。没想到中途被其父发现,迅速拦截还二话不说刮上耳光。
众目睽睽。
纯不哭。
纯的眼睛像能拂逆所有落魄的情绪,我第一次看她那眼神是她被赶出家门的那天。她站在门前,我踮脚从窗户中偷看——
没一丝可怜更没哭闹,反倒是我从铁罐里掏出一块饼干偷溜出去。
“吃吗?”
不为所动,眼神很硬 ,我干脆把饼干塞到她手中,又偷溜回去……
不吃。
她好像天生就有一条“硬”根子,一股狠劲,像当下她用手掀起我的裤裆试图嗅味,我拿她没撤,“好吧,我回去换。”
(2)
纯认定的事好像从没输过,她考试常考第一,与男生踢球,踢大前锋。打篮球,三步上篮。身高要比同龄人高,比我高半头。
“小不点。”
她喜欢这样喊我,然后追寻远方的夕阳,光芒流泻深处。我会跟上她的步伐来到边上,陪她看日落,眺望缥缈的远方,还会问:“小岛外的世界会是怎样?有没有不吃鱼的猫?”一直好奇,因为岛里的猫都特别爱吃鱼,家里附近就有几只,面熟了也就算了。
“外面的世界应该有它们吃不完的鱼。”
“会胖不?”张手比划。
“那是猪好吗?”
“那这样呢?”我缩小一圈。
“或许……”她不再看我,“它们早就吃腻了,慢慢就不吃了。”
“那它们会吃什么?”
“像那里的人一样,吃特别精致的东西。”
精致的东西?当时我无法理解什么是精致,我只想知道:“纯,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小岛?”
据悉纯的父亲曾离开过,其父曾是村里的文化人,教书的,还被评为优秀老师到外培训。不幸的是那次培训和城里人发起嘴角,说他是浑身鱼味的土包子,说他的文化是假文化,还差点打起架。因此性格开始乖戾,已有一女还冒起风险生二胎,仍是女,接着教师职位被辞去,同时遇上计划生育,怀上纯时全家东躲西躲……认命了,是鱼味土包子的命……全家慢慢以出海捕鱼为生。
可纯从不那么恨自己的父亲,看见他还会喊早安,不躲避很直面,偶尔还帮忙做手工制品……斗笠、草鞋。算不上是爱,更像一个小小的女孩以怜悯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父亲,看到大人中的无奈、悲鸣、执着——
纯比所有人都成熟。
这事我很早就意识到。
她第一次来月经也很早,十一岁就开始有胸,头发很长。班上男生的目光会随她的变化而变化,不是色眯眯也非恶俗。纯比同龄人都快褪去稚气,睫毛稍卷,眼神不羁,属于看久了也不觉腻的女生,所以但凡早熟的女生笔下的东西往往迷幻,同龄人描叙天空还是蓝蓝的、白白的,而她的笔下:无垠的天幕架起一副罹难已久的灵魂。
全班作文比赛第一。
全校作文比赛第一。
全镇作文比赛第一。
又是同年她有机会到城市参加作文比赛,有机会尝试离开这岛……
离开那天学校还组织少先队员欢送。从村里的小路开始奏乐送纯上船,这过程纯的父亲始终没露面,纯一如既往的从容,与母亲拥抱,依次大姐、二姐。到我的时候,她不拥抱也不说话,抿了抿嘴上船,那么的平静又带点执着,我猜大概还是有点恨我……
因为出发前一晚,她与父亲有了争吵,父亲不让她去,她不从——
“城市不是你这种人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爸,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但人心依旧!”
——声音很大,没多久纯就被赶出家门,手背一淤一青,一如多年前月光迅速注满她的锁骨,她一动不动地杵立、不依仗外墙、不落魄,同时又别于过往,这回我看见她落泪。
第一次。
泪很浓,像汲满一管的墨汁从眼角里迫不及待地挤出。我又偷溜出去,只是所攥的不再是饼干,她躲避我的目光,她懂得什么是落魄什么是窘态,我还强行把纸巾塞到她手中。
她是攥住了,但不擦,还愈发使劲。
“难道她是女的,你就要这样对她?!难道曾经你在城市被人笑话土包子不配有儿子,你就一辈子土包子下去!”是纯母亲的声音,从屋里渗出,依附到那夜的风……成了刀,呼啸而过。
其实类似的风在纯回来那天也刮起。我正打算接她船,后知后觉她已回家。村里没少先队的号角声、没欢呼。这年的小岛要比往年冷,而纯依旧单薄,即便我看见她时嘴唇已抹上淡紫,她不颤栗不叫我,从狭窄的巷道往上眺望,灰色的天空是道疤痕,慢慢与她的青春有了契合——
没拿到名次,就连安慰奖都没有。老师也觉得可惜,据说那天她来月经,疼得太厉害无法下笔,交了白卷。我特别能理解,所谓的理解因为是猜到因由,比赛题目:《我的父亲》,字数不限、文体不限……
纯脑袋无限空白,一无所获……
本以为。
(3)
后来我看见她开始读信。
“谁写的?”
她会把信揉成一团,“无聊人写的无聊信。”
但这些“无聊”没像垃圾、落叶,它们成了红疹,越挠越多,越来越多,一周一封,到一周五封、十封。密密麻麻。
纯面对这些小家伙慢慢不随意,她会折飞机抛向海岸,折叠些小玩意和我玩耍,但最近一次她开始把信收到身后——“关你屁事。”
几次下来我算看见写信人的名字——小南。
小南是那次比赛所认识的,是城里人也是那次获奖者。纯没向我过多描绘小南的外貌,她简单而言:很酷,长刘海。我迅速脑补,三个字:陈浩南。那回流行古惑仔,流行长头发,纯的打扮却没像陈浩南的女友细细粒,她的打扮有点野,放假时会到村口染一头金发,再将新的白色校服裁短,往衣角处画四叶草。
当时的纯是学校里风云人物,有的人会喊她大姐,也有人喊她纯爷,对她追求的人狂蜂浪蝶。她钟爱小南,她读小南的信会笑,没拘束、露齿、声音张扬的笑。
“小南真有这么好?”
“你不懂。”
“你不说我怎么会懂。”
“小不点,好好读书。”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我有啊……”
相应的,她的成绩从全级前十降至中层,父亲对纯的态度没愤慨没怨恨,她不打纯,纯不抬杠,看似和睦,但两者间已横亘摸不着的釉质并不断矮化这段关系——
纯与这家庭间的关系。
有些卷子需要家长签名,她会找我帮忙。
“小不点,你的字写得真好。”
她不清楚,我曾用一个暑假模仿她的字体。包括,“小不点,长得挺快的。”她也不了解每逢放学我会打球,还有……若一个女生过于早熟,后来的高度就会提前停止,纯从曾经班里坐最后的位置慢慢靠前……到我上初中那年,我已高过纯,而她没变……依旧那样,那样如此,那样的倔,倔得无法让人理解,喘息。
(4)
那是一个暑假。
那年的暑假有点特别,小岛新增了码头,还通了商,开始有游客来小岛玩耍观光,又是那年我见到他——
那束长刘海顺延轮廓,不厚重不稀薄,鬓发乌黑落于耳垂。不邋遢,没胡渣。我真没见过这长相的人,小岛上的人大部分偏黑、邋遢,而他犹如一圈光,毛茸茸地从海岸倾斜而来。没痞子味,不邪恶。白色的衣裳搭配午夜绿的短裤,硬要说形象上的缺点,个头不高,但非常落落大方站在纯的旁边,当时的纯不从容不自然,眼眸中的“硬”泛软了,或者说彻底坍塌,现在的她太像太像一个小女人……
“你好,我是小南。”他主动上前。
“你好……我……”语塞并略带咯噔,小南还友好地伸手,我犹豫了……良久才颤栗对之,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握过任何女孩的手……
小南是女的。
“她是女的,你没看出来吗?!”
事后纯曾描述我当时的表情,就像人类遇见外星人。瞳孔放大,眼皮下拉。但纯那回的语调很轻,她说她爱她,她小小的年纪就能分清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
“喜欢只是想见她,但爱却是想拥有。”
那年的暑假小南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小岛。她思想成熟,这成熟非佯装。我见过不少同龄人要么学大人打扮要么学大人口吻,而一个思想真正成熟的人会有着不轻不慢的温柔及体贴——
出去吃东西,她会递纸巾;走在街上她会示意我们靠边;纯看见心仪饰物,她使坏不买,过后又偷补。我和她单独相处过,她一方面有着女孩的温柔另一方面又有男孩的刚硬。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
她知道我说什么,回答轻松,“其实不该说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应该说什么时候敢自我面对。”
“你们这样会有幸福么,纯可是个女孩啊……你也是女孩啊。”
她撩了撩发丝,撩发丝的姿势也一点都不娘,“这么说吧,我和你的区别只是你的蛋蛋不用钱,我的蛋蛋要钱。”
“意思是……”
“以后赚到钱我就做变性啊。”
我第一次知道“性”是可以变,好像小岛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些措辞、或者种不允许有人说这样的话,但不可否认小南真是一个能迷倒女孩的女孩,偏偏又是名女孩……
因为在其他人眼里,尤其小岛上这或许是海妖对纯的惩罚。说当年纯带头抗议,这事海妖尽收眼底特意派一个城市的女孩来毁掉纯。传多了,她爸也按奈不住了……
(5)
我记得那段时间纯常被赶出家门,其父年纪上来了,打是打不动的,与其说纯被赶出来,倒不如她自个也不想回去。她站在门外,不那么从容,从傍晚熬至夜深,每次如此,眼角眉间长出忧伤,久而久之她开始会拿些信件,小蓝的来信,一字一句地默读,看起来特别劳累,好像最好的年华因爱而变成飘渺的浮沫……
后来有一夜,该是来月经,她满头汗珠,手背捋了又捋,依旧密麻。最后不得不半蹲,咬牙切齿。
我倒了一杯水,她不喝,她仍是不想获取施舍,她不想自己的落魄在别人眼里晕染,即便是相识已久的我,她仍不愿意……
那晚我把杯子一直握在手中,我想通过“握”保持水温。
她说:“小不点,你觉不觉得我很傻……”
我听得出这非疑问更多来自喟叹,毕竟她的倔强无法成为密不通风的铠甲,多少有点流言蜚语渗到心坎。
“你有喜欢过人吗……”她看我没反应又问了起来。
我摇头,动作迟疑……杯子的水冷掉后我又回去倒。
她不喝,重复了第三遍她再问:“我想要一根烟……”
我从家偷来一根,刚想起没拿打火机,她索性把烟含在嘴里,半晌又握于手中,拿烟的姿势别于大人,不是夹的而是托的,类似托起一把步枪,对准摧枯拉巧的周边,又像手掌被凿下一道深深的瘢痕。
不再言语。
再然后……没有然后了……
纯离开了这岛……
她离开的这事最大的震惊是没有震惊,家里人对学校说孩子不想念书,学校也不管,当时的纯成绩已垫底,她身上早与优秀无关,她给人的形象都是尖锐、极端,这形象学校甚至觉得会影响其他人。
母亲为了调和纯与父亲的事也累了,或许纯的离开能够给家人一种平静甚至解脱,据说触发纯私自离开的主要原因是父亲为纯安排了一场婚姻,小岛上的人都比较早结婚,先订婚等孩子长大点便结婚,关于礼金纯的父亲已收了些许……
然而这小岛上也许唯独我最为焦急,一天下来四处问船家,据船家描述纯离开的那天没带什么,是清晨的船,很少人会选清晨离开。
雾大、冷冽。
“她穿得厚吗?”
“那小姑娘好像不怕冷,好像没什么知觉。”
“怎么会没什么知觉呢!”我有情绪,可这情绪终究无法持续……就像纯离开后她会给家人寄信,我打听发现来来去去都是:别担心。我慢慢的记不起哪天起她不再寄了,有人传言她死也有人传言她和小南一起私奔。头一年我都是这样认为,认为她们挣脱世俗的目光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我当时还相信童话、相信小说。
直到我看见小南,她来小岛找纯,她说纯曾在信中说要找她,也约定一个时间到码头等她,没出现……一直没有出现,包括后来那些年都没有,她真的消失了,彻底的消失……
纯消失的这些年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孩,是名男孩,只是出乎意料的是她父亲没想象中那样愉悦,男孩叫:春。生于春季。
我多少读懂这名的含义,他曾问我纯会到哪看落日还会做什么,偶尔我看见他一个人拖起逐渐驼背的身躯缓慢走到边上,浑浊的眼眸往浩瀚的大海望去,泛白的发丝那么的硬又那么的稀疏,或许他不曾意识,其实纯只是像他,太像他而已……
而我偶尔想念纯也会到边上,我真的有很多很多话想对她说,我想说现在已长到一米七五,如果你看见我这样子会不会还叫我小不点;我的成绩能排在全年级前50,都听你的,好好读书了,但没选择到城上读书,一方面经济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小岛的旅游业越来越好。
小岛从默默无闻的地方成了国家二线旅游景点,没有人会想到十年后的小岛真不再靠出海捕捞来生活,每年都有大量的人过来旅游,而我做起了导游,介绍我们村介绍海岸线介绍你曾走过的一些痕迹……
有一回我看见特别感人的一幕,有位小朋友主动叫其他小朋友别往海里乱扔垃圾,她说大海是人类的母亲。
我问谁教你说的。
“妈妈。”
我有点不礼貌地反问:“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总觉得她会是纯的孩子,看见爱护海洋的小孩我都觉得她是纯的孩子,而且我知道纯为什么没找小南。小南曾说那天自己没准时赴约,临时有事,找了妹妹先去,小南的妹妹和小南是双胞胎,我见过一次标准的女孩,小南以为纯看见她妹妹就会主动叫上,因为两者太像。但我猜也许小南不曾想过纯大概因此抛弃了她,以为小南彻底恢复女孩身,不想打扰,因为她是一股狠劲的人,狠得总以为自己的逻辑是对的……永远的对。
但这也仅是我的猜想,谁也没见过纯,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还活着……
风从海边吹来。
吹乱了海水,吹乱了小孩粉红的裙摆。
“叔叔,我的妈妈叫……”
还有我的目光……
听首歌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