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展览开幕,出现了这样的宣传词:“鲁迅的文学,字字句句震聋发聩,令人深思;蒋兆和的画作,一笔一墨震憾心灵,令人回味。”其中,“震聋发聩”是成语“振聋发聩”的误写,“震憾”则应写作“震撼”。这两处误用虽然被视为错得离谱,不合语文常识,其实也暗藏了“正误”之间的语义联系和历史演变痕迹,并非仅仅是写错别字这么简单。
先看“振聋发聩”的误用。“震聋发聩”容易蒙混过关,主要靠了三个条件:
一是“震”产生他动用法。古汉语中,“震”本是自动词(如“地震”),“振”是他动词,即“使之震”(如“振铎”,意为“摇铃”)。可见古人早已知道声音来自“振动”或“震动”,且声音确实是(自)震动和(他)振动兼有的。现在的“震”也有了他动词的用法,例如“震动全社会”“震撼全场”等。
二是动结式的发展和高频使用。按今天的用法,“震聋”是动结式,意为“震动而使之变聋”。而“振聋”是动宾结构,“振”是及物动词“振动”。“聋”是受事宾语,意为“失聪状态或失聪者”。二者的结构和意义都有差别。但“震聋”这个组合本身的接受度已迅速提高,这与动结式的发展有关。动结式约在南北朝时产生,在现代汉语中已成为高频使用的结构,甚至发展出一些只能做结果补语的“唯补词”(刘丹青,1994)。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补语构成的动结式有高度的词化倾向。“震聋”这样的二字组正是动结式的原型形式,“聋”在语义上又很容易被理解为“震”的结果。
三是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名词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例如,单音节名词的活动受到较大限制,而名词双音节的静态比例最高(王珏,2001)。现代汉语母语者更不倾向于将单字“聋”理解为名词性的“失聪状态或失聪者”,因此“振聋”“震(振)聋”都不易解读为动宾结构,使两者相混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但是,虽然“震聋”在现代汉语中有了合法的身份,“震聋发聩”似乎也能顾“形”思义,但“震聋”(动结式)与“发聩”(动宾结构)结构上不对称,不符合成语的构造规则,尤其重要的是两者的意思相反——震得变聋和振动得让聋人听见。因此,“振聋发聩”是不能写成“震聋发聩”的。 再看“震撼”和“震憾”的混用。
与“震”~“振”类似,“撼”~“感”也是同源字。我们认为,“感”由他动用法发展为自动用法,且由“撼”分化他动用法。“憾”则可能是“撼”的被动意义。下面具体分析。
据王力等主编(2016[1979]),“感”最初意为“使人心动,令人心情起变化”,如:
(1)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经·咸卦》)
(2)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感”为“互相感应”,《易经·咸卦》)
后来“感”成为自动词,有了不及物用法,意为“感触、感动、感伤”,如:
(3) 木石犹感,而况臣乎!(《晋书·谢玄传》)
(4) 定省无期,勒玆贞琬,感而增涕。(《大唐故韩府君墓志铭并序》)
“撼”是他动词,意为“使动”。《广雅·释诂一》:“撼,动也。”王念孙疏证:“《说文》:‘?,摇也。’?与撼同。”
(5)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
(6)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宋史·岳飞传》)
这些“撼”例偏向物理的“动”,而物理的“动”跟心理的“动”本来就是相通的。英语自身移动和使移动都是move,感动就是moved,用的是同一个词。而“感”也有物理动作的用法,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无感我帨兮”(引自宗福邦等主编2003)。当“撼”用于“心灵震撼”时,又回到心理之动了。
据郑张尚芳(2003),“感”为侵部见母上声,“撼”为侵部匣母上声,匣母主体在上古是ɡ-声母, “感”和“撼”之间是清浊交替,这是上古汉语区分自动和他动的典型形态手段。中古群母(ɡ-)只有三等韵,一二四等变为中古匣母(?-)。但匣母的ɡ-声母在南方方言中仍多有保留。如“厚”在温州、无锡(老派)的声母就是ɡ-(详见李荣1965的讨论)。另外,詹伯慧等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对“厚”的记音显示吴闽语较多地保留了群母字的塞音读法。再如北部吴语“懈、澥”的白读基本保留声母ɡ-。如白读的“懈、澥”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保留ɡ-声母,读为[ɡa]类音,如“懈脱勒(上海)”表示“浑身没劲”、“澥脱勒”表示“由稠变稀”,也指粥饭菜肴变质变松出水,或“关系由密切变得疏远”。其实“澥、懈”也是同源字,分别用于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懈”就是精神上“澥”了,只是有时切分不那么清晰。李荣主编(2002)显示,,“懈、澥”对ɡ-声母的保留,南至宁波,北至丹阳(不含)。丹阳的“懈、澥”是k-母,发生了清化。这是因为丹阳属于“吴头楚尾”,说的是不典型的吴语。所以,在温州方言等吴语中,“撼”的声母是?-,在上古应该就是ɡ-,与见母的“感”(k-)是清浊交替。
“憾”在从心的“感”字上又叠加心旁,显然是后起字。“憾”可能来自“撼”的被动意义,意为“内心受到撼动”,如:
(7) 子翼詈人,人都不憾。(《新唐书·刘袆之传》)
“憾”在上古是侵部匣母去声,而“撼”是侵部匣母上声,仅声调不同。根据潘悟云(2000)、郑张尚芳(2003)等的观点,声调不同在上古是韵尾的不同,上声是[?]尾(更早可能来自[q]尾),去声是[s]尾。这是一种韵尾交替的派生形态手段。非去声到去声的变化常标记基本词的滋生过程(可参王月婷2008的综述与讨论)。“憾”是古代“恨”的近义词,其语义特点是表示一种事后留下的心理状态,也是心理受到外部事情影响的一种表现。
从论元结构来分析,“撼”是及物、使动性的,“震动而使……撼动”,“憾”是不及物、被动型的,是“受到震动而被撼动”。它们围绕“感”组成了一个语义相关的同源词族,本质上属于语态(voice)范畴的区别。这是单用时的情况。但是,在结果补语的位置,由于补语语义指向的多样性,这种语态的差别是可以被中和的。例如“看懂了这本书”,“懂”是及物的,“懂了这本书”;“翻烂了这本书”,“烂”是不及物的,是“这本书烂了”。在这一背景下,古代出现过“震憾”的说法,实际跟“震撼”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在现代汉语中,这个意思已经统一规范为“震撼”,不再用“震憾”了。
总的来看,“感”从他动词发展为自动词(并由“撼”分化他动用法),“撼、憾”在主动、被动“态”上的区别,都由语音形式这一典型的形态手段编码,与论元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但这一过程早早完成,在汉语中不复能产。而且,从上古至今,汉语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若非专业研究所需,这一形态手段早已无迹可寻。如今,类似“撼—憾”的分工属于以汉字字形弥补“态”编码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提高书面表达的效率,在口语中几乎没有作用。
另外,“感、撼、憾”是心理动词,对心理动词有诸多讨论角度,其中之一是“刺激物导向(stimulus-oriented)”和“感受者导向”(experiencer-oriented)的分化。“感”的变化是由“刺激物导向”转变为“感受者导向”:早期的他动用法属于“刺激物导向”,后来的自动用法属于“感受者导向”,由形态手段编码。“感”的分化和转变与现代英语相似,只不过英语采用的是屈折形态:心理动词词根是及物动词,是“刺激物导向”。用于感受者时采用分词形式。以与“感”语义相近的“move”为例,它的词根是及物动词“move”,用于感受者时需使用过去分词“moved”。
(8) a. It moves me. b. I’m moved.
现代汉语也有“刺激物导向”转变为“感受者导向”的倾向,虽然没有形态手段编码,但“感动、烦、奇怪”的最终结果都作用于感受者,如:
(9) a.这件事很感动我。b.我很感动。(10) 我很烦,因为你很烦。(11) 我很奇怪,因为你很奇怪。
相应地,现代汉语出现了完全“感受者导向”的心理动词,如“忧愁”,这是词汇语义对形态手段缺失的弥补。但有时“愁”又较低限度地兼有他动用法,一般仅限于“愁人”。
(12) a.*这件事很忧愁我。 b.我很忧愁。
总的来看,将“zhèn聋发聩”的“zhèn”记作“震”,将“震hàn”的“hàn”记作“憾”,反映了汉语历时演变的某些特征和特定范畴编码手段的转化。但是,基于对成语构造规则的尊重和对语义表达准确性的保证,我们还是建议正确书写“振聋发聩”和“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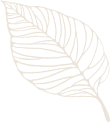
参考文献李 荣 1965 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第5期。李 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刘丹青 1994 “唯补词”初探,《汉语学习》第3期。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王 珏 2001《现代汉语名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 力等主编 2016[1979]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王月婷 2008 上古汉语动词内的达及态构词,载潘悟云、陆丙甫主编《东方语言学》第4辑。詹伯慧、张振兴主编 2017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宗福邦等主编 2003 《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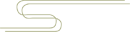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吴越,博士,2019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网信室编辑
今日语言学
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长按指纹,识别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