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周说A”更多精彩哦!
大串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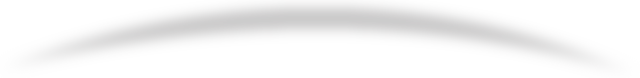
不过,这些组织最红火的时候,还是在八月份,八月以后,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就奔赴祖国各地了。
第一次串联是在八月底,大规模串联还没有开始。所谓大规模串联,是说火车开了专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大串联中的红卫兵
我和一些初二的学生一起,第一站到了西安,在西安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的大标语满街,写的是打倒刘澜涛和霍士亷,这两位,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的两位负责人。
从西安一下子杀到了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的,那时的火车慢啊,似乎坐了两天两夜。因为大串联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坐的是旅客列车的硬座车厢,和旅客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兴学雷锋,我还提着个大水壶,不断地为旅客们倒水。尽管不断走动,但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下车时,发现脚肿了。
在乌鲁木齐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吃羊肉。那时的新疆很富庶,我们住在八一农学院,牛奶随便喝,羊肉随便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晚上总跑厕所。后遗症是我现在不吃羊肉。二是我们被新疆人围在八一广场,因为我们要炮轰王恩茂。
当时,“炮轰某某某”是常见的口号,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先炮轰一下再说。当时的解释是,炮,是毛泽东思想,轰,是衡量,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其实,谁也经不起这样的炮轰。

王恩茂(右)和赵锡光
王恩茂是新疆的最高领导,当年在著名的359旅,他是和王震曾经是多年的战友,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管理新疆很多年。没想到他在新疆威望很高,当我们喊出炮轰王恩茂的口号后,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不干了,他们围着我们和我们辩论,说,我们看你们不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你们是台湾来的特务。他们还有一个说法,王恩茂是新疆八百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孩子,哪里知道王恩茂到底怎样,反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出声保的人,我们都敢碰。没想到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2007年,为了撰写王震百周年的纪录片,我又到了乌鲁木齐,时隔四十年,这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我说的变化,还不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能够感受到的内心的东西,脸上的笑容,民族的和谐,领导人的威望,这些,似乎被一场刮了四十年的风一点一点刮走了。
1966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1月,我都在忙于串联。开始还说是播文革之火,后来就纯粹为了玩了。当时我的原则是去远处,今后不太方便去的,除了乌鲁木齐以外,还去了广州、锦州等地。
大规模串联开始以后,开了很多红卫兵专列,因为人多,车厢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我常用的一个办法是钻到三人座椅的下面睡觉,幸亏那时我的体积没有现在这么大,不然,钻也钻不进去。
大串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步行,也就是那时所说的“长征”。
文革初期,其实就是个深度洗脑的过程,共产党的一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一切,都要深深植入孩子们的脑袋。毛泽东的每段语录,都像雨露,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比如说:长征是播种机。
为着这句话,好多孩子行走在路上。
我们第一次选的目的地很近,是天津。但是,走到通州,就走不动了。关键是军心瓦解了。怎么办呢?就近拦车。有个同学叫陈志刚,外号小瘸,其实他不瘸,但是也不刚,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学他拦车的那句话:我们走不动了,帮帮我们吧!结果是没有成果,车都是呼啸而过,也许因为我们人太多了,谁也不停。于是,不知道谁说,附近有火车站,坐火车吧。坚持走到火车站,看见一列客车静静地躺在铁轨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管他开到哪里!
结果,火车把我们拉到了锦州。
那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
第二次长征,到了1966年的11月间。当时,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也就是说,免费的火车,免费的住宿都没了。我们几个同学不甘心就这样停止了如此美好的生活,商量着钻个空子,不是没有免费火车吗,我们长征。
这次选的是从西安到延安,大约一共760华里。我们六个同伴,都是14岁,每人只背一个书包就上路了。记得第一站住在三原,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这是冯玉祥三原誓师的地方,而邓小平留学归来,第一份工作也应当和这里有渊源。
我们没有看到历史,却是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在三原我们多呆了半天,为农民拔了半天的萝卜。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居然还收到了农民寄来的感谢信。

我们当然也不是光做好事,也做坏事。在快到延安时,我们在户县住了一晚,那时已经很冷了,我们几个躺在炕上,实在扛不住了,决定点火烧炕。当地农民应该是很少这么早就烧炕取暖,就是取暖也是在灶上烧饭同时取暖。我们情急之下,在老乡门后拿起一些白色的秸秆就塞在炕洞里,点着了火。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麻杆,应当是农民还没有剥过的。
不过,当地农民很淳朴,他们给我们开了窑洞的门,很放心,再也没来巡视过,我们一早起来,迅速出发了。
路过黄陵时,我们还和当地的有关领导见过,为什么见,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一点,这儿有狼。
当天,我们恰好又迷路了,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预定要住的那个村子。那是个叫后河南的村子。
黄土高坡上,过一个沟壑就是一马平川,只有再下到一个沟壑,才想起刚才其实是在山上。那个晚上,月亮冷凄凄挂在天上,我们走在类似深沟的一条小路上,路边高坡上草已经枯黄,夜风吹得这些草沙沙响,在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有些瘆人。忽然,扑棱棱一阵响动,吓得我们浑身鸡皮疙瘩,原来,是我们的脚步惊动了一只山鸡。
我们提心吊胆地前行,像那只惊恐的山鸡。
这当口,后面匆匆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去哪里,自告奋勇带路。我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好紧,生怕这是个地主分子,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加害,于是,我手里抓了一块石头,走在最后面,眼睛盯着这个带路人。
说实话,在黄土高坡上找到一块有杀伤力的石头,难度还挺大。不过,还是白找了,我们看到了村庄,闻到了炊烟的香气,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这一路,还是经历了不少故事,760里路,我们六个14岁的孩子,徒步走了九天半,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我们曾经饥一顿饱一顿,曾经睡在草堆里,在一个叫甘泉的地方,我们六个人盖了一床被子。
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场景,回到北京,我回到家里,妈妈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心疼地看我浑身不得劲,问我,是不是长虱子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一轱辘爬起来,说,快把衣服全脱下来,扔到阳台上去。
果真长了一身虱子。后来,身上还长了疖子,化了脓。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大夫,大夫直摇头。给我挤疖子时我还是很坚强的,大夫的称赞现在还记得:这孩子真勇敢,长大能当解放军。
其实还用长大吗,两年后,我就穿上了军装。
在延安的事情可以忽略,无非是看宝塔山,喝延河水,瞻仰枣园,每个去延安的红卫兵都是这些节目。从延安回来是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铜川上火车,这也是中央觉得再不这样的话,学生们野掉的心很难收回了,于是用各种办法把学生找回去。
这是1966年的11月中旬了,陕北已经冷了。我还是光脚穿一双布鞋,就是当时北京小孩喜欢的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那种懒汉鞋,一身单衣。车到洛川,大家下车上厕所,我的鞋掉了,光着脚在地上走,我居然没有感觉,原来是冻僵了。
三十年后,1996年底,我作为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组委会秘书长和现场总指挥,又若干次走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那些地名,三原、黄陵、甘泉、富县,听着都是那么亲切。
每一条路,都不是白走的,这就是长征给我的启示。
→点击阅读原文,访问“钝角网”,获取更多精彩文章!
钱跃君:欧盟新总理将走马上任,欧盟正逐步转变为统一的联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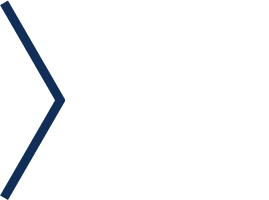


让 常 识 说 得 更 有 底 气!

周说A
——周志兴的微信公众号

周而复始,继续说常识ABC!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