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是一片平白无奇的世界。
成片的“巨树”高耸云天,在它们脚下,矮了不少的“大树”更加浓密。对于我来说,这两个都是不可企及的高度,只能偶尔仰望到它们的顶端,如同头上有了两重天。“大树”的高度,基本是我身高的500倍,而巨树就更恐惧了,是我身高的30000倍! 这片世界,叫做丛林。高耸的巨树才是树,我眼中的那些“大树”,其实只是灌木丛。 没错,我是一只卑微的小蚂蚁。 这片丛林有着固定的法则。对,就是常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生存,我们蚂蚁成群结队的忙碌不休。别看我们卑微渺小,身高只有一毫米,但寿命最长也能活七年。不过这是在群居的前提下,如果谁胆敢孤身出走,那只能存活几天,很快就over了。 说到生存,这片丛林有着很固定又很无奈的设定:最无敌的是狮子,它们体型巨大,差不多300公斤左右,这可是我一只普通蚂蚁的1000万倍!而且它们更是凶残成性,所有肉类动物都是它的食物!咳咳,当然不包括我这种蚂蚁,即便成千上万滚成一个蚂蚁球,都不够狮子塞牙缝儿。比狮子差点点的是豹子,而豹子下边应该就是狼,再往下是跑得很快的羚羊和长得很高的长颈鹿一类的。根据体型大小并结合生猛程度,以及吃肉还是吃草等来区分,形成了这种由高到底、由强到弱的顺序。

这种根据弱肉强食而来的设定,便是所谓的丛林法则,形成了一条“生物链”,据说是可以从上到下来次第鄙视的,也叫“鄙视链”。 不过,作为蚂蚁的我,基本无权参与这种无聊的“鄙视”,不是不想,而是那些站在最高处的狮子,根本看不到它们脚趾缝儿里的我,因为狮子是“野兽”,而蚂蚁是“昆虫”!这种比“鄙视”应该更具伤害力,叫“无视”。说实话,我们蚂蚁对于这种伤害从来无感,试问在这片丛林中,哪有蚂蚁愤慨过狮子的历史? 也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傍晚,我也曾羡慕嫉妒过狮子那种昂首阔步的王者姿态,落日的余晖在它们身上镀了一层金边,同时在我们脆弱的蚁穴周围形成大片阴影,令人心悸。这种阴影从现实潜移默化到内心,时间一长,似乎也就习惯了。 所谓法则,如何制定估计司属于造物主,所以顺应丛林法则的生物链,从来不包含蚂蚁愤慨狮子这种无用条款,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说我没志气是吧?我现在刚爬到一棵巨树的中间,正好指给你们看,在遥远到几百米的天边,几头雄狮正在攻击一只高大的长颈鹿!

要说这只长颈鹿也够勇敢,碗大的蹄子玩命乱踢,有几次都把狮子踹的非常狼狈,然而用处并不大,七八米高的身体内蕴藏的无穷气力最终耗尽,也没逃脱被狮子撕碎成条状午餐肉的命运。它们残忍而犀利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却让我内心的那片阴影更加沉黯。 试问长颈鹿都不能幸免,何况身为蚂蚁的我?

好吧,作为丛林铁律的“生物链”中,有一条更为悲催,能否站到顶端,最终比的不是个头“大小”,而是性情是否“凶猛”。长颈鹿虽然比狮子高大好几倍,但吃草的佛系性格是终极弱点,根本不是王者该有的特质。
“性格决定命运”,果然没错。而亘古不变的丛林法则,真的是无处不在,又惨烈至极。 算了算了,我是正在劳碌爬树的小蚂蚁,给你们指的却是几百米外天边的事儿,说那么远干嘛! 我虽然够小,但却很忙,都是为了那该死的两个字:生存。狮子们傲视群雄,却叽叽歪歪说它们那也是为了生存……别闹了!我们蚂蚁管那种叫“生活”,这里明显是两个概念,最高端的生存,才配叫生活。我是一只小蚂蚁,此生的最高希望,注定只配追求生存。然而很多时候,生存这种希望,也会被随意“践踏”成无望。 那一天,我们家,成了“斗兽场”。 准确的说,我们家那一片“辽阔区域”,成了数只狮子争夺交配权的战场。一时间“战火纷飞、尘灰冲天”,获胜的狮子一脚踏平了我们的家!不对,应该是一脚踩碎了我们的蚁穴,让它从三维立体成了两维平面,隔壁的傻叉老王,楼上的帅逼小张,楼下的肥婆老……,反正整个村子毁了一多半,估计死了十几万!最可恨的是,这只挨千刀的狮子经过惨烈战斗之后,还竟然浑身抖动几下,喉咙里发出“骚气十足”的低吼,然后更恶心人的……哦,然后更恶心蚂蚁的是,它撒了一泡“骚到天边”的尿,整个村子全完了! 果不其然,最凶猛的,一定是最骚气的。

当然,我非常幸运,被冲天的灰尘吹到半空,又摔出很远很远!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到底有没有想过反抗,譬如在空中亮出嘴里白皙的小獠牙什么的,只是摔出的遥远距离,已经吓破了我的“蚁胆”。别看只有三米,那可足足是我身高三千倍的距离!如果不是我身轻如燕脸上都是三角腹肌,假设也像你们那样腰间自带泳圈儿、脖子自带软枕的话,早特么摔碎成一地纳米级的渣渣儿了。 这就是有一副好身体的好处,咳咳,我虽然摔的很远,但不是很惨,马上翻身跃起,还能跑的屁滚尿流,啧啧啧,羡慕了吧? 别羡慕到一嘴涎水好不好?我的噩梦已经开始了。别看我们蚂蚁群居中能活到7年,但离群后的个体最多只能活几天,这都是因为失去了组织! 劫后余生的我拼命逃离危险区,面临的却是更大的危险。 平时用须子天线交流的同伴没有了,首尾相接留下的一长串气息痕迹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别笑话我,你们人类也一样,你们现在交流不也是更多依靠手机里的天线吗?你们外出不也是成群结队在高速上排成一长串吗?从自己活腻了的城市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城市瞎逛,还美其名曰叫“旅游”,在我看来也是无聊致死的逃亡,哼! 算了,我是一只失去家园的小蚂蚁,再大声叽歪,想来你们也是听不见的。其实还有比失去家园更悲催的,狮子王在我家那片“狗斗”,踩碎了我的家园,踩死了我数十万同伴,事先都没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压根儿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有句很时尚的俗话能够形容我此时的心情:再牛逼的肖邦,都弹不出我的忧伤。

总之,我一个人……哦不,我一只蚂蚁,是活不长的。望着遥远到几百米外的天边,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看到或看穿更远的世界,但是起码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是早几个小时或者晚几个小时的大概率。
蚂蚁的死亡也有N多种打开方式,常见的无非是饿死,或者被兽类踩死,这只是永远上不了头条的普通现象,而非吸人睛目的新闻。最大的概率,是被天上经常落下的“水流星”砸死、淹死,别忘了,那种被叫做“雨”的水流星,比我的身体也大了无数倍。 然而,我的人生也和你们一样,既富有哲学性又充满戏剧化,细思之后都是情理之中,然后遭遇又在意料之外。看到天上滚雷阵阵,我最怕被密集降下的水流星砸死,却万万没想到正好相反。 原因还是来自于那场毁了我家园和同胞的“狮王争霸赛”,其实争的就是两样儿:更多的交配对象,以及为了这种交配而需要的更大空间。没想到吧?这么恶心的事情,也能说得这么文明。不过我的死活和这件事没直接关系……问题出在狮子王获胜之后,马上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利,开始那个啥了。 这场丛林大火,我真的没说是因为狮子王和“王妃”们擦出的爱情火花,而是怀疑老天爷都觉得它们太嚣张,开始天打雷劈了。关键还是这次老天爷又劈歪了,“轰隆隆、咔嚓”……该死的狮子王安然无恙,近在咫尺的一棵巨树却应声倒下,烈火熊熊! 这下晕了。 老天爷确实牛逼,能在下雨的同时还一边下“火”,触怒上天的狮子王也怕了,拔出作案工具回身就跑,带领一大群王妃,拉出一长串烟尘很快就没影了,在我眼中,真的堪称“一骑绝尘”。 我也急了,感觉到狮子王一阵疾风掠影从我的宇宙上空驰过,也顾不上它会不会把我踩成一张0.001寸的小照片,果断跟在它身后追了过去。咳咳,这个顾虑似乎有点多余,估计一时半会追不上。

我知道狮子王要逃到这片丛林的边缘,才足够安全。那里有一眼都望不到边的“大水”,对的,那是大海。我们村曾经有过一次整体远距离搬迁,哦,和你们的被动拆迁不一样,我们是主动搬走的。我有幸成为先遣队的一员,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在悬崖上看到了那片大海。大家毫无疑问的群情激动,天生习惯沉默是金的我们,第一次叽叽喳喳,纷纷憧憬着把新的蚁穴建设成上百层的“海景大别墅”……
“滚粗!”我们先遣队的大队长怒了,“你们白痴哇?这海边的空气又咸又骚,有事没事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服的知不知道?而且风很大,我们爬半天悬崖,经常会被风吹落回原地,如果赶上台风就更苦逼了,会被吹的无影无踪,保证连你妈都找不到。” 被领导巴拉巴拉一顿训骂,我们毫无疑问的热情变成了毫无意义,不过也有同伴小声“神戳戳”的反驳,“那些近乎神一样的人类,不都对所谓的海景房趋之若鹜吗?”大队长一听暴怒,“神一样的人类,也有傻叉知不知道?” 听完大队长的话,即便它在骂完“神一样的人类也有傻叉”时也后怕得看了看天空,但我们还是表示信服,放弃了在悬崖边建设“海景蚁穴”的打算,认同那片大海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对于我们蚂蚁来说还是太危险。 所以,我下决心逃向海边,按理说该纠结一番。屁股后边的丛林大火在“火速蔓延”……这个说法很形象,又快又危险,就像面临大小俩王组成“王炸”的地主,而我是手里就剩俩3的农民,一个3代表苦逼,一个3代表绝望。而且天上还有密集的水流星轰炸,即便追随狮子王的脚步逃到海边,横竖都是一个死!然而好死不如赖活着……哦,这个词儿对眼下来说不够应景,应该是早死不如晚死,这就是所谓的“求生”。 其实,我的转身逃亡更多是无意识的,也更多是无意义的。 把整片丛林都蹂躏到不停“噼啪”哭喊的邪火,蔓延的速度超乎想象,估计火舌已经舔到了我玲珑凸翘的小屁屁,烫的“老子”直咧嘴巴,一张脸都快撕成两瓣了。 其实我想多了,那只是大火蒸腾过来的滚烫空气,形成了飞窜的热风,再次把我吹上半空,无限小的身体无法呼吸,无限大的思维也陷入混沌……准确说我是被烫死的,足足几十秒之后,尸体才化为一小小小缕灰烟。 这世间,据说有那么几个老头,大家谁也没见过,但好像又都听说过,有的穿袈裟有的批麻布什么的,他们对不同的群体念叨过差不多相同的一句话:有信仰者得永生。我是一只渺小的蚂蚁,按理说没啥信不信的,但似乎在我死后,真的进入了“永生”的循环之中。 这种说法很模糊,而我当时也迷迷糊糊,感觉到了一个很豪奢的地方,到处舒展盛开着大红大绿的花和叶,巨大的铁罐子里飘出的香气很是刺鼻,桌子上摆着有点变质的猪肘子啥的,还有各种发硬的动物形象的面点,而且捏的一点都不像,简直丑的一比。桌子后边有个金灿灿的塑像高高在上,我莫名知道那其实是个肥头大耳的泥胎,比那些动物形态的面点还丑。 此时的我,正在金身泥胎的脚下,从一块石板的下方往上爬,石板上阴刻着八个字,是一堆曲折的“弯弯绕”,我在“弯弯绕”的金色凹槽里向上爬,这样虽然更费时间,但比在光滑的黑漆平面上省力,还不会跌落。 我顺着八个字的最后一个从下往上爬,而跪在桌前的两个人,却在从上往下念: 佛法无穷,有求必应。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脖子上戴着光闪闪的银项圈儿,很是刺眼。然而可惜的是,他表情呆滞愚钝,显然是智力发育有问题,正被他的父亲使劲按住脑袋,双腿就像被打折了一般跪了下去,而此时父亲脸上无比虔诚,看上去比他儿子还要愚痴呆滞。 父亲碎碎念着那八个字,想来这个傻小子和我一样,听得清,却搞不懂。我只是本能的往上爬,他只是被动的往下跪。我好像刚爬过“必应”俩字,正处于什么“有球没球”的那个地方,他正好腿折了一般跪了下去…… “咣、咣、咣……”,倒霉的钟声突兀响了起来,这下把我的小心肝儿给吓得,一把没抓牢,被应声震落!“咣当”一下砸在小孩的额头上。好吧,那是该死的钟声,只靠我一只渺小蚂蚁更加渺小的残缺魂魄,是搞不出这么大动静的。 更令人惊奇的还有,我刚落到傻小子的额头上,他的倒霉爹地就按着他本就白痴的脑袋开始撞地球,这次是真的“咣当”一下,把我生生拍成了一张0.001寸的小小小照片! 最倒霉的还是傻小子,这特么给撞的,额头上立刻冒出半个鸡蛋大的包,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给撞死球了……哦,是昏过去了。用这么大的劲儿,一看就是亲爹。我甚至估计他这是故意的,就是想借着磕头撞死这个“瓜娃子”,正好把“杀子”的罪恶黑锅让那个金身泥塑来背,自己回家再和老婆重新折腾出一个不傻的。 这是尼玛什么狗屁爹地呀!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哦,他是人,不是兽。 此时,从里边跑出一个老光头,也被傻小子嘴里冒出的白沫儿吓“傻”了,就跟被传染了一样。但当对上邪恶爹地虚伪的悲痛眼光,智慧如他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光头,马上看穿了一切,不过然并卵,估计这口黑锅他是背定了的。老光头气了一个半死,但好在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虔诚”搞晕,马上一跺脚,说要去搞一瓢冷水把这傻小子浇醒! 我cao,这特么老光头比凶残的爹地还邪恶呀!这冷飕飕的山顶,我可是连个裤衩都没穿! 我赶紧一骨碌爬了起来,抹了一把唇边还没干的白沫儿,指着身边那个凶残的家伙大骂:“你特么什么狗屁爹地呀?想要撞死你小爷儿我呀?” “啊?谢天谢地,你这是真的灵光了呀!”邪恶爹地突然痛哭流涕,自己跪下不停撞地球,老子突然“灵光”一现,按住了他的脑袋狠狠撞了下去。 一报还一报行不行? “你……撞我的脑袋干啥?”邪恶爹地似乎看穿了我已经看穿了他行为的行为,有点恼羞成怒却不敢发作,因为我已经成为传说中的佛系灵童,咳咳,就是和那个金身泥塑属于一个系列的意思。 “切……”我白了他一眼,握紧脖子上的银项圈儿,“这个玩意儿还是我的,不能像你昨晚打算的那样,拿去卖了交租子。” “好吧。”邪恶爹地咧着嘴巴回应,又黑又瘦的脸皮差点撕成两瓣。 哦,大家不用惊讶,我原来那只渺小的蚂蚁魂魄,已经被砸进了傻小子的脑袋,我现在重生后的身份,姓马名义,字润……之,我噗,牛皮吹大了,那个光闪闪的银项圈儿透露了我的秘密,是姓马名义……字闰土。

贰 然而,这一世叫做马义的我,虽然不再是个呆滞的傻小子,但那缕蚂蚁的残魂还是格局太小,纯属被那个光闪闪的银项圈儿蛊惑了,不然打死都不会“托生”在他们家。 因为,太太太特么穷了呀! 跟着邪恶爹地一路走回家,我才知道什么叫“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哦不,应该是穷到击穿了我想象力的底线。看似随意挂在我脖子上的银项圈儿,原以为就是个普通玩具,没想到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哦,又跑偏了,是这个家里唯一像点样儿的值钱东西。 我前生向往大海的意念,上苍似乎理解的太简单粗暴了。新家的确在海边,但一点都不“新”,那叫破的一比,就是两间“破”茅草房呀!炕上只有一床露着黑棉絮的“破”棉被,盖住等着穿我的“破”裤子出门的黑妈咪! 全家就两条到处都是破洞的裤子,谁出门谁穿!咳咳,如果放到2019年,那真算时尚最前沿,可惜,眼下只是二十世纪的开端。 看到这一切,我十三岁的脸上瞬间布满和年龄不符的表情,最牛逼的肖邦,都弹不出我的沧桑。大家都羡慕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作为卑微的蚂蚁灵魂,我本以为“银项圈儿”也不错的,这算是造化弄人咯? 穷就穷吧,还偏偏种瓜!在离海边不算太远的沙地上,租种了几十亩地,我现在的苦逼人设,就是个在茅草屋里看守瓜地的“瓜娃子”!emmmm……我看着手里用来插沙鼠的三尺钢叉,一门心思想插进自己的喉咙里。纠结半天,我的蚂蚁魂魄里莫名冒出一句话:死都不怕,你还怕活着吗?哦,牛皮又吹大了,实话实说,是叉子上残留的沙鼠血迹吸干了我的勇气,还没插自己,先吓了一个半死。 算了,前生是只卑微的蚂蚁,这一世虽然也是“马义”,毕竟是人了呀,闰土闰土,土点就土点吧,“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回算是很应景。虽然没死成,但生活还是穷的半死,粮食那可是“硬菜”,更多的是捡回来的瓜皮,吃的小爷儿我眼珠脸皮都是绿的,还带着黑黝黝的条纹儿,他母亲滴! 不得不说,那个又黑又瘦的“妈咪”对我是真好,她名叫“六斤”,这毫无个性的名字来自于出生时的重量,她经常偷着炒一些黄豆粒给我吃。然而,这种平白无奇的“舔犊之情”,还被叫做“九斤”的奶奶广为诟病,只要看见我吃豆,就是那一句“吃饱了瓜皮还要吃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把老子气的呀!只能躲到乌桕树后骂一句“你个老不死的”。 然而骂归骂,“九斤”奶奶都80岁了偏就不死,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很多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其实并非我的蚂蚁灵魂天生不懂孝道,而是她有两件事让我厌恶,都和我“吃饭睡觉吃豆豆”不相干的。一个是她不喜欢洗长长的裹脚布,真的很臭!一个是经常阴恻恻的辱骂疼爱我的黑妈咪,而且为她毫无理由的责难找出了理由,说什么“她年轻时婆婆就是这么骂过她的,这是天生的规矩”。听到这句话,我灵魂深处似乎传来一个声音:这种自上而下的规矩,难道也是上天赋予的?那和我还是蚂蚁时的“丛林法则”是不是一样? 这种少有的思考很费脑筋,似乎也不是我渺小的蚂蚁灵魂能够理解的层面,让我很是闷闷不乐。坐在月光下的海边,颈子上的银项圈儿和层层波浪海天一色,咳咳,这样的美景都无法消解我内心的沧桑。耳边并没有“苦痛的沙,吹疼脸庞的感觉”这种忧伤,更生不出“我们的征途就是茫茫星辰大海”这种豪迈,因为都是属于有钱富人闲到蛋疼的赶脚,和我这种穷人无关,眼下这种“茫茫星辰大海”,除了用来自杀,看不出还有其他用途。我内心似乎有了一种感悟,这凡世间99%的问题,都是因为没钱造成的。我看着手里的钢叉一脸的嫌弃,老天爷,不要让我像个海夜叉,给个三太子敖丙的角色好不好?即便坏透了也没啥,我真的是穷怕了。 这些日子,唯一让我有点欣慰的是,一直惦记着把我弄死的邪恶爹地不再想那事了,反而盼着我快点长大。我内心不由发出一声冷笑,不就是想让我替你多出力气种瓜吗?搞的就像你有多大家业等着我发扬光大一样,你以为你是累死很多职业经理人的某健林、我是睡遍全国脑残网红妹的某思聪哇?要说这纯属我蚂蚁灵魂的心理阴暗,也没错,这人穷点不是问题,而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才是问题呢。 不再邪恶的爹地变着法的讨我欢心,竟然让我坐在装满西瓜的板车上,拉着去赶集,看着他瘦骨嶙峋的后背上不停滚落的汗水,也就没那么厌恶他了。当然更多的厌恶是转移了,转移到了路上那些收税的家伙们身上,一路上被拦下来好几回,好像他们分属不同的组织什么的,根本不是一拨的,足足交了半车瓜钱才来到镇上,我觉得他们比夜里成群偷吃瓜的沙鼠还可恨,捏着钢叉的手心都出汗了,好在我没有失去理智。 镇上确实热闹,爹地也确实改恶从善,没再去酒馆“排出手心里的四文大钱”换黄酒喝,跟我一起认真经营西瓜摊。此时,来了一个手托鸟笼的家伙问我:“瓜娃子,你的西瓜多少钱一个?”我听完就怒了,他身上溜光水滑的绸子大褂既没有补丁更没有破洞,令人生厌,但紧接着我脑海里“灵光一闪”,回头问车后搬瓜的爹地多少钱一个,爹地回答四文钱,我假装傻啦吧唧没听清,面对鸟笼男挑中的七个西瓜,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三文钱一个,你给二十五文钱吧。鸟笼男听完就乐了,说好一个瓜娃子,就给你二十五文钱。望着他带着瓜皮帽儿的背影,我狠狠啐了一口:我呸,你特么才是瓜娃子! 邪恶爹地彻底震惊了,连声赞叹我不愧是“佛系灵童”转世,我们在路上商量好的卖瓜方法果然很有用,一唱一和之间,连这样有钱的聪明人都给忽悠了,其实一直卖的就是三文钱一个,这下我们不仅多赚四文钱,对方还像得了便宜一样跑的飞快。我斜了一眼爹滴,很邪性的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有钱人都聪明了? 不得不说,我莫名其妙有了一种快感,但明显不是来自这多出的四文大钱,更不是因为爹地震惊后的赞美,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许源于我的灵魂深处,感觉那个穿着丝绸大褂的有钱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这种穿破裤子的穷人聪明,这种类似于前世“丛林法则”的东西并非颠扑不破的铁幕,这次我撕开了铁幕的一丝缝隙,故此愉悦。 然而爹地的快感却是极大,简直到了兴高采烈的程度,望着远处在风中飘飞的酒旗,咬牙忍下肚子里肆虐的酒虫,给了我四文钱说你去买个两文钱的白面饼,剩下两文去书楼,边吃边听。我到了那里才知道,并不是什么喜马拉雅听书啥的,而是位于街角的平台子,一个叫做“阿鼓”的家伙,骨瘦如柴的小身板上套着满是补丁的长衫,扯着脖子唱“京韵大鼓”,那面小圆鼓夹在胳肢窝里,都特么快敲破了,旁边一个叫“阿伟”的小伙子拨楞着单弦伴奏,唱的却并不是“重整河山待后生”之类,而是在叽歪什么外国又运来了多少洋米洋面,比我们穷老百姓自己种的还便宜,我们即便是大丰收了但还是要吃苦受穷。

这段书文,阿鼓唱的咿咿呀呀,我却听得心惊胆战,冥冥之中,似乎都能涉及到我前生后世很多内容,但于我只是一种莫名的灵魂触及,我并看不到全貌,更无法预知未来。 我在震惊中有点走神,但不知道是因为他没说清楚,还是我的蚂蚁灵魂格局太小,总之并不能抽丝剥茧洞悉一切。台下的老百姓更没耐心,打算丢鸡蛋……哦,鸡蛋那么金贵是不可能丢鸡蛋的,丢的是瓜皮。阿鼓一看不行赶紧换了内容,改说什么在我们大清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段子,小小的日本竟然凭着举国之力干掉了庞大的“尼姑拉屎”云云,台下的听众这次买账,越是血腥的内容越是喜欢听,一个个听得满脸放光激动不已,咳咳,那瓜皮丢的更厉害了。 然鹅,台下一个从东北逃难来的老太太哭了,说日俄两家“瘪犊子”在我们大清的地界打仗,根本没和我们大清国商量,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被无辜炸死,最后尸体的胳膊腿儿都凑不齐了。听完这些,我的好心情瞬间低落,并不是因为远在东北的什么战争,也不是因为阿鼓的声音太过难听,因为台下的叫好声更难听。而是灵魂深处又突兀响起那个声音:前世我家的蚁穴毁于狮子王的“狗斗”,它们在我家打仗就根本不会征求我们蚂蚁的意见。那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使然,可现在我们都是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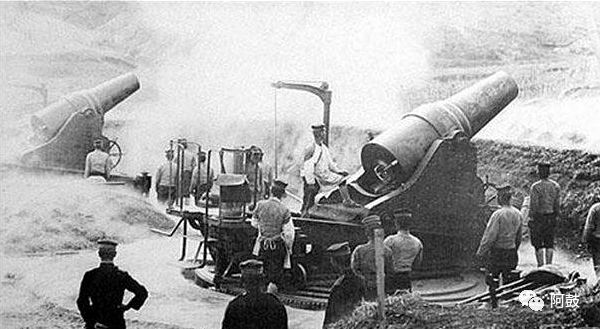
这个感觉非常之郁闷,越是想不明白越生气,比我嫌弃爹地穷还厉害的那种,气得我转身就走,偏偏这时阿鼓端着破碗要钱,老子一块瓜皮砸到他脸上,转身就跑了。
回到家里,被海边风吹日晒搞成碳一样的黑爹地和黑妈咪,一边分着吃我带回来的白面饼一边抹泪花花,爹地把我作为“佛系灵童”坑了有钱人的故事说的活灵活现,整个破茅草屋里充满活跃的气息,却让我有点想钻地缝的无地自容,索性又跑到月光下的海边思考人生。越想阿鼓唱的破玩意越觉得不对劲,前世被狮子王“狗斗”踩碎的蚁穴,和这一世被日俄蹂躏的东北,总感觉有某些相似之处。倘若这堂皇的人世间,还和以前的“丛林”一样的“法则”,那做人和做蚂蚁又有何区别? 沉黯宽广的大海不时泛着银光,似乎昭示着我思考的问题有了某种宏大的味道,却更加晦涩难通,注定我这样小格局的蚂蚁魂魄无法破解,也注定了我这次的不快乐会持续很长时间。 一门心思讨我欢心的爹地开始发愁了,直到年底才想出一个主意,让我去帮地主家照看祭祖的供品,还巴拉巴拉做起了思想工作,意思说我看管瓜地的经验很足,两者在技术层面都是一样的云云。我听完就怒了,说你个老不死的想啥呢?那么多好吃的放在那里发霉发臭,我是“佛系灵童”又不是特么“净坛使者”,两者的职能和内涵相差万里,我如果最后忍不住,偷吃了人家祖宗的伙食,会被打死知不知道? 结果,爹地被我一通巴拉巴拉给忽悠懵了,却红着脸继续叽歪,直指我看管祭品是防老鼠来吃,和看管瓜地防沙鼠吃在技术层面即便不属于一脉相承,也算触类旁通或者举一反三啥的,然后我偶尔偷吃几个权当百密一疏,可以把罪过记在老鼠账上。我听完就给气乐了,说当初你在庙里打算把我拍死在地上,然后让佛祖背黑锅就是这个套路对不对?这下爹地的尴尬表情亮了,竟然大言无耻的赞叹,说你不愧是“佛协灵童”,这个都知道哇? 这种少有的父子深度交流人生,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但爹地最后提出另一个理由,说地主家的小少爷会从城里来乡下过年,我可以借此和他一起玩耍成为朋友,更说人这一生有多大未来,就看你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这让我有些震惊,都怀疑老不死的以前也是什么“佛协灵童”了。然鹅爹地矢口否认,拍马屁说他的深度都来自于我这个“灵童”儿子。好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还是虚荣心作祟,默认了这种逆向影响带来的光环。 我们租种瓜地的地主家在周庄,算是家大业大,祭祖的供品五牲俱全颇为丰盛。然而都快被我吃完了,地主家的小少爷才到,长得白白净净,名叫“迅哥”。看到他让我眼睛一亮,莫名感觉,似乎能够看到他很多未来的脉络,称不上预知,但比我自己的都清晰。不过这小子虽然本性良善,开始却根本不信我的忽悠。我说倘若我把你的面相看的很准,你就替我背偷吃供品的黑锅行不行?结果他挡不住可以害死猫的好奇心,咬牙说……那好吧。 于是乎我开始忽悠,说别看你现在温文尔雅,长大了会比泼妇还能骂人,迅哥一听就火了,说你个偷吃供品的瓜娃子扯淡!我说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你长大了骂的可不是一般人,都是祸国殃民的政客和无耻下流的伪知识分子,这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无畏。这下迅哥高兴了,祠堂里似乎都充满了鲜活的空气,他说其实我觉得吧,你说的都对。看看,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果然是有道理的。 于是乎我再接再厉,说你以后能成就超级大学问,做政府文化大员,虽然从未有耐心写长篇,但中短篇依旧会流传后世、滋润沧桑,而且包括你说过和没说过的很多话,都会让后人拿来满天飞的扯淡等巴拉巴拉,先娶朱安……咳咳,是朱丽叶一样的传统大家淑女,然后睡自己的时尚美女学生等巴拉巴拉……
结果迅哥听得一愣一愣,激动到脸绯红心狂跳,已经被我忽悠的找不到北了,很难相信自己的人生能有这般惊险……哦,是这般精彩。虽然我知道自己“佛系灵童”的头衔纯属胡扯,但毫无影响我扯淡的超高水平,中间还把自己看管瓜地、用钢叉刺沙鼠的无聊过程,以及在雪地上用笸箩捕捉麻雀的事儿演绎到无比魔幻,毫无经历的“迅迅初哥”每每听的眼睛发亮,而我则被桌上的供品噎到只翻白眼,他也当做没看见。 当然,看管供品驱赶老鼠的工作,也干的稀松平常。我冥冥中好像听阿鼓说过什么《普京传》,据说那位大帝级别的人物小时候也天天打地鼠。哦,这感觉好奇怪。 我唯一令迅哥不解的是,从来不说“云云”这类的词汇,直接说巴拉巴拉,让他感觉很是新鲜,可能歪打正着,触动了他以后反对旧文化的逆骨。总之他再也不用“土弟”或者闰土来调侃我,仿佛我比他还要更前沿一些。甚至我因为爹地喊了声“土儿”,就抓起钢叉把老不死的追出了周庄,迅哥都没看做是大逆。更甚至我在偷喝了供酒后指着他鼻子,说你应该懂的你的人生有多大未来,就看你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这种牛逼话,而陪着我喝趴下的他竟深以为然。结果第二天醒来回味之后,我瞬间吓尿,好在破裤子上到处都是洞。 美好的生活从来短暂,爹地对于我吃胖了的身体很是惊恐,死拉硬拽把我拖回了家,我眼泪汪汪对迅哥依依不舍……更准确的说是对满桌子的供品。 回到海边,思考人生的无聊再次把我淹没,半个多月的净坛使者生涯,可比佛系灵童实惠多了,这让我对未来更加迷茫,变得茶饭不思、忧伤不已。废话,吃惯了大鱼大肉,谁还有心思吃瓜皮呀!换谁都会郁闷半死的,我愁的头发都……哦不对,不是头发白了,是胡子都长出来了。作为佛系灵童的爹地,已经用尽了自己的造化,再也找不出让我欢心的办法,更不知道我忧伤的原因。不得不说还是妈咪心细如发,不仅没有跟着我一起忧伤,反而大胆做出惊喜判断,他的佛系灵童儿子…… 思春了! 我去,这是啥判断呀!我当时爬石碑的庙里,又不像未来迅哥笔下的阿Q,能够看到尼姑啥的,妈咪这不是乱劈柴吗?我根本不是什么“思春”那么大的境界,只是思念那些供品美食好吧?不过妈咪坚持并偏执的认为,“思春”和“思念好吃的”是一脉相承的俩概念,就好像吃饱了必然想那事儿,正所谓“饱食思淫欲”,我想了一下颇有道理,也和迅哥一样开始脸红心跳了。 此时,我这个假“佛系灵童”真“净坛使者”的存在,在我们村早就出名了,卖瓜忽悠有钱人的故事被妈咪“自卖自夸”,成就了贫苦人家鲜有的“智慧美谈”,连最初的呆滞痴傻,都成了佛系灵童厚积薄发前的“大智若愚”,试问穷人家的孩子哪有这么邪乎的?然后提亲的媒婆纷至沓来,都深信我的未来必将不同凡响,结果家里的破门槛都被直接踩碎踏平了。好吧,即便有前世“蚁穴”被狮子王毁掉的阴影,但还是欢迎现在这种另一类型的“踩碎踏平”。 不得不说,她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好姑娘,放弃了嫁入“小富农”家庭的机会跟了我,估计这是她一生犯过的最低级错误,没有之一。过门之后,她充分展现了一个传统妇女的无上美德,“吃瓜受累无怨无悔”,大部分时间一个人操持十几亩瓜地,让我有更多时间坐在海边假装思考人生。 真特么作孽呀! 然鹅,还有比作孽更作死的,我们村子附近有句恶俗的土话,叫“吹灯抱媳妇儿,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灯油很贵,生活很累,贫苦人家真心没啥其他娱乐,更没有避免怀孕的措施。孩子一二三四连续出生,都是嗷嗷待哺的嘴。到了小五小六一生下来,我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她撒谎说送给了有钱人家,可那些饥荒灾年,最不值钱的就是这些刚出来的小生命,听说很多都被直接丢进海里…… 我快在崩溃中发疯,或者在疯狂中崩溃了,横竖都一样。这种痛苦最能吞噬生机,我在无数次恍惚中甚至觉得,眼下的人生,是不是还不如前世的蚂蚁?

迅哥在他以后的文中悲叹我的遭遇,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非常鲜活的形容了我的忧伤和麻木。再牛逼的肖邦,即便能弹出我的忧伤,也弹不出我的麻木。其实迅哥不知道,他对我非常失望,而我对他更加失望,他在思想上走向富有,却在经济上日渐凋敝,我多希望反着来呀!能让我抱一抱他的大腿,即便发展成为邪恶的某思聪我都不在乎。然而世事无常,我这个假“佛系灵童”不仅灵气儿早已消失已尽,连善恶的底线都被生活踩碎踏平。 迅哥还说我选了他家祭祖的烛台拿回家,感觉那够愚昧,其实他根本不懂,我是在回味当年的“净坛使者”生涯,如果非要赋予这烛台于祭祀的原味功能,那我打算用来祭祀我一世枯萎的青春,零落的梦想。以及把它在祭坛点亮,看看能否照亮我再一次转世的方向。在我的想象中,那将是一个衣食无忧、安全恣意的全新世界!
为此,我甘愿违心的祈祷,哪怕让我的蚂蚁残魂在冥冥中颠沛百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