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 GAS

当当当,打铁啰!
俗话说:“世上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一语道出了打铁这个行业的艰辛。由于没有机器助力,打下料、热熔、打扁、剁尖、做弯、蘸火等工序都要靠人力完成,铁匠铺里一年到头熊熊的炉火、当当的响声、铮铮的铁骨……
金华打铁店最多的时候,有过四五十家, 但那是上世纪80 年代的事情了。这些年, 传统的打铁生意已陷入困境。昔日的手工打造,许多已被机械化制造所取代。木炭改用了煤炭,手拉的风箱变成了电控的鼓风机……尽管与时俱进,但还是逃不过逐渐被淘汰的命运,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还有铁匠这个职业的存在。随着打铁的生意越来越清淡,很多打铁铺都关了门,现在剩下的,可能也就澧浦、孝顺、蒋堂还有几个老人在打铁。


2018年8月30日,浙江金华兰溪梅江老街上唯一家抽老风箱的打铁店,成了即将消失的风景,因而引得各路人马前来怀旧。铁匠铺起源于古代,也称“铁匠炉”,所谓“铺”,也只是一间破房子,屋子正中放个大火炉,即烘炉。炉边架一风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膛内火苗直蹿。
土灶旁的风箱木柄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变得光滑无比。它是由木箱、活塞、小风门构成的,用鼓风的原理使灶火旺盛的一个助燃装置。别看风箱结构简单,推拉起来真挺费劲,快慢缓急,快拉慢推,很费臂力。上世纪 80 年代风箱曾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烧饼店、豆浆店、崩爆米花的、补锅的……大多数家庭烧火做饭都得拉风箱。

砍柴上山
文:寿昌建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一项让人望而生畏的苦力活,那就是上山砍柴。
我的老家是个小山村,出产番薯、玉米, 柑桔,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旮旯地方。三十四年前, 人们一年四季,烧饭用的大多是稻秆麦秆。没有煤没有煤气,更没有电器,柴禾是惟一的能源, 也是除粮食外的头等大事。
我家兄弟三个加上父母五口人吃饭,一日三餐,柴禾需要量很大。母亲操持家务,最烦心的就是柴禾。很小的时候我就为母亲烧灶火, 她在灶上煮饭炒菜,我在灶下添柴加火,如果柴禾准备不足,遇到雨天或雪天就得烧湿柴, 每每母亲在灶上忙碌我却将灶里的火烧灭了, 米下了锅没火就会夹生或糜烂,母亲便会生气地唠叨:“平时不多准备些柴,这时候就让我受罪”。她一脸愁容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那时的农村,山路边、田埂边的杂草像被剃过头一般,牛羊吃、大伙割,光秃秃的,就连刺人的荆棘也被割得干干净净。母亲说:“松毛、杂草用来引火最省力,荆棘烧起来火旺,而且烧炭也非常好。”邻近的杂草割完了,我们就惦念着离村三四里的茶园。茶园是外村人的,平时缺少管理,草盛长,灌木多,是我们分外眼红的割柴的好地方。可看山的老头就是不让外村人进园,每每看到我与小伙伴偷偷摸摸进了茶园,老头就会扯着大嗓门叫喊:“割草的小孩又来了,还不赶快走?再不走,我没收你们的钩刀,罚你们放电影。”吓得我们屁滚尿流。有一次,小伙伴还慌不择路从高坎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
那个年代,农民过日子的开支,除了养猪、饲鸭、放牛来挣钱,砍柴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生产队里做工分都是点人头的,由队长或会计记账,谁也不能缺工。哪家哪户想弄些自己的生计做做,只能在生产队出工前和收工后想办法。我的父母亲都是善良朴实的庄稼人,整天没有一丝空闲的时候。母亲常说:“小孩子不知数,睡到日头上山岗,我们大人已经做了半天生活了!”在半天“生活”里,父母不是割猪草、挑大粪、锄地,种些蔬菜瓜果,就是在山脚、坎上、路边割杂草,作为烧火的柴薪。

我家的自留山林远在十几里路之外的百药尖,那里有一大批连绵起伏的山脉,真称得上一句:山叠山,岭重岭。高山险峻,怪石崚嶒, 著名的景点“神丽峡”就跟这片山脉连在一起。上山砍柴,最好的季节是在秋天。春季,山上的树木都在蓬勃生长,再加上春天雨水多,砍下的柴水分重,烟气大。秋天枝干叶燥,我们选择上好的花梨树、板栗树和其他杂树砍下几根,再将硬柴砍成五尺来长,将枝枝柴扎好, 然后一个个地背回家倒在柴屋里,等到了冬天, 那柴就枯得相当好烧了。
自家生火做饭,多半用割来的茅草和毛柴。那些从山上砍下来的好柴禾常舍不得用,省下来出卖营生。八月秋天的“八月柴”,杆粗叶壮, 齐刷刷地竖立在村里的明堂里,晾干后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各家的墙角,上面盖上茅草或者破塑料布,等赶集的时候再运到黄宅、潘宅甚至是义乌后宅镇的“树市”去卖。
平时父母总记得赶集的日子,农历三六九是黄宅市,一四七是潘宅市,二五八则是城里的集市。每当到了集市日的头天晚上,父亲会比往常早些入睡,为的是第二天赶个早市。我们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恍惚中听到“嘎嗒” 开灯的声音,昏黑的老屋有了隐约的亮光,床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父母亲蹑手蹑脚地起床了。水缸舀水的声音、木柴折断的脆响、母猪讨食的嚎叫,依次传到梦乡里。父母忙活了好一阵子,天光才渐渐发亮,村庄里开始人声狗叫,慢慢地热闹起来。

柴火装车是一个力气活,也是把式活。堆积的柴薪经过几个月的挤压,不再蓬松,变得扁平且有形,如同母亲说的“火糕”一般。父亲把一捆捆的柴薪堆放在手推车的底架上,粗壮的绳索绕过高高的柴薪,穿过手推车的顶梁, 母亲瘦小的身体就趴在柴薪上,“一二三”父亲喊到“三”,母亲就用尽力气扑压一次,父亲的绳索就勒紧一次,那“嗯哧嗯哧”的声音在清晨显得特别沉闷。天寒地冻的,紧绷的绳索,深深地嵌入肌肉,看父亲偶尔皱起的眉头, 一定是勒得父亲针扎般的疼。半个时辰后,车座上原本高高的柴薪变成了压缩饼干,车架两旁柴薪终于堆装平衡了。看到柴火装得有棱有角,父亲又插上一些粗壮的枝条进行打扮。母亲说:“看相好,就会卖得快。”此时,父母的额头都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子。父亲折身回到屋里吃了简单的早饭,走到手推车边,系上背带, 挺起腰板上路了。在晨曦的光影中,父亲魁梧的身躯渐渐成了背影。农村的小孩贪玩也贪吃,我琢磨着跟着父亲去赶集。可是母亲执拗着不让我跟班,总说:“小屁孩跟去只会赖吃添乱, 啥事也做不了,不许去。”
长大到十五岁时,我才加入了和父亲一起上山砍柴的行列。
砍柴的日子,父亲会提前一两天就将砍柴刀磨得亮闪闪。然后,带上“稻憃”( 一种比一般的扁担或者木棍相对要粗大一些的棍子 ),堩索。砍柴时候脚底下穿的,必须是特地为砍柴准备的“草鞋”( 这种草鞋是名符其实的“草鞋”, 用稻草、破布条编织 )。在漆黑的夜里,我们父子就推着独轮车出发上路了。
凌晨三四点钟,在路上甚至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天上的一轮残月,朦朦胧胧地照耀着前进的道路。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小道上山,起码得翻越好几道山梁,才能最终到达那一片属于我们家的山林。上山的道路总是崎岖难行,山虫“知知知”地叫声,让夜山更加寂瘳。
等到费尽周折艰难上山以后,天才破晓, 晨光熹微,一轮红日从远方东边的山上喷薄欲出。来不及欣赏山上的美景,我们马上分头行动,开始砍柴。一个人,一个上午必须砍好属于自己的四捆柴。父亲的柴捆相对大一些,我的柴捆相对要小一些。四捆柴砍好,差不多就到了正午。带到山上的饭菜,此刻都变成了冷饭,但天底下最美的食物,并不是出自于名厨的手下,而是来自于饥饿,就着山沟里的泉水, 那真叫一个甜!
砍柴虽然辛苦,但爬了那么远的山才赶到这里,谁不想多砍一点呀?所以,下山的路上, 几乎每个人的柴担子都超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挑着柴担前行,肩上被棍子压着的地方, 就像一只凶猛的藏獒,正用它那锋利无比的牙齿在啮啃。双腿踩在岩石上,小腿肚弹棉花似的弹个不停,颤抖个不停。一直要到把柴放到山下的独轮车上,人才轻松许多。到家以后, 往往落霞满天,太阳已经平西了。
我高中毕业后当兵,后转业,母亲也由柴而煤而煤气、电饭锅,再无柴禾之忧了。然后我对柴禾的那种感情随岁月的流逝反越来越深。犹记得,下山途中,撑杵稍歇,西沉的太阳照在村庄田野上,看炊烟袅袅生起,搜寻自家的一缕,想象母亲灶上赶烧晚饭的样子,感觉异常甜美而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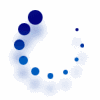
杭州燃气集团提醒
长按扫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