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活动平台

《也许人家原本就是一颗猕猴桃》西北工业大学 吴闻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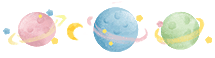
有很多同学和我聊到过他们的烦恼,关于集体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关于大学中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舍友。
有的嫌弃舍友打呼噜说梦话流口水磨牙放屁。
有的抱怨舍友不洗澡不爱干净乱扔乱放东西。
有的讨厌舍友作息混乱开夜车睡懒觉影响休息。
有的腻烦舍友贪小便宜不爱分享老用别人东西。
有的看不惯舍友太好看,有的看不上舍友长太丑。
有的嫌舍友话多,有的怪舍友沉默。
有的认为舍友重色轻友,有的觉得舍友自私自利。
如此种种……
和谐融洽的宿舍总是相似的,而不和谐融洽的宿舍总是各有各的原因。一些宿舍中,舍友们的不一样成为相互眼中的“欣赏”,再不济能算“可爱”;而另一些宿舍则会让这种不一样演化为彼此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我看来可以和“婆媳矛盾”相媲美——在朝夕相处的人眼里,你的任何特质和缺点,似乎都会无以遁形。
但同学们,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不管舍友是你的“欣赏”、“可爱”还是“矛盾”,在若干年后当你们作为校友重聚时,他们都会是你们最想见到和拥抱的人。而那些现在你看来无法忍受的缺点,终究会成为彼此宝贵的故事和谈资,让你们从嬉笑聊到流泪。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曾经就有一位奇异的舍友,而且我打赌你们没见过这样的。
所以今天,不讲道理,讲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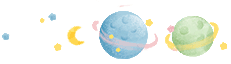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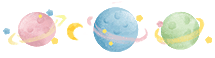
01
那天中午,很热。
一个小时前我领到了宿舍钥匙,热情的学长把我送到了宿舍。我擦干净床板,正坐着凉快会,宿舍门开了。
一个满脸胡渣的人走了进来,他穿了一件貌似是90年代初的咖啡色的化纤衬衫,一条老旧的格子短裤,灰色的丝光棉袜几乎套到小腿肚子上,踩在一双橡胶凉鞋里,头发看起来至少两个月没剪。
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喊了声:“叔叔好”。
他径直坐在了邻床,没答应我,也没看我一眼。
02
这个被我叫“叔叔”的,其实是我的舍友。
我们尴尬的第一次见面,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不修边幅,二是他真的很不修边幅。
他叫阿伟,来自因为高考而被大家熟知的那座县城的那所著名中学,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没到过那座县城,没去过那所中学,但你一定练过他们的“兵法”,也被他们成堆的卷子折磨过。
军训时,阿伟剃了头发,刮了胡子,这时便能看出他脸型极方正,脸与额头和下巴的拐角几乎是90度,标准的长方形,很像我买的第一部国产手机。
阿伟的一切行为也是极方正,方正得怪异。他走路时目光总是死死地盯着前方,绝不左右顾盼。说话时无论句子长短,永远有一种报手机号码的节奏感。
军训时阿伟和我并排站,队列训练阿伟一直是同手同脚,却非常认真卖力,摆臂力道巨大、幅度超常、握拳坚硬,但因为和大家是反方向,所以次次铁磁地抡在我手上,一天下来我手就青了,如此这般惨无人道地折磨了我十余天。
后来阿伟进了飞虎队,因为极不协调。
后来我也进了飞虎队,因为手疼。
备注:飞虎队,是由进不了队列汇报表演的军训不优秀分子和伤病员组成的特殊团队,美其名曰“飞虎队”。
03
阿伟对自我卫生的管理,远不止“不修边幅”那么简单。
事实上阿伟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不爱干净的人,没有之一,而且我一度怀疑阿伟心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干净卫生的概念。
前面提到的阿伟的丝光棉袜,整个大学期间,我只见过他有两双。
第一双,阿伟会穿整整两周才换下来,把它平整地压在床褥和床板之间。两周后,会把第一双取出来穿上,把另一双换下来压上。每次压完后,说实话,除了气味以外,真的看起来会和新的一样。
我印象中阿伟一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袜子,如此往复,我们见证了两双袜子如何能从灰色变成黑色,从黑色变成红色,从红色变成肉色,最后变成彩色;我们也忍受了两双袜子如何能从汗臭转化为卤臭,从卤臭转化为尸臭,最后成了我们无法形容的气味。
04
阿伟不仅不洗袜子。
床单、被套、枕套、衣服、裤子、内衣内裤、鞋子,一律不洗。
印象中阿伟第一次换床单已经是大二下学期了,学校发的那条浅蓝色的床单,从军训开始睡了快两年,上面本来积下了一层看起来油腻腻的污物,后来睡着睡着又给磨去了。
有一次宿舍剩下的6个确实看不下去了,逼阿伟至少洗了内衣裤。阿伟没有肥皂和盆子,我们6个就抽签出了一个盆子给他。阿伟接了一盆水,不会洗,就把衣物放盆里泡着,后来就忘了。
两周后宿舍馊味难忍。一排查,找到阿伟那盆衣物,居然已经长了一盆绿毛。场面太过惊悚,我们6个又抽签出了一个人,捂住口鼻连衣带盆一道扔了。后来又觉得不负责任,这得消毒深埋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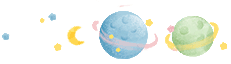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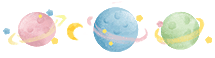
05
关键是澡也不洗,当然也不洗头。
军训暴晒,被那绿皮外套捂出一身汗也不洗,淋了雨馊了也不洗,暴晒又干了背后都结了一层盐也不洗。
第一次洗澡是被哥几个硬拽去的。阿伟连块香皂都没有,进了澡堂就一动不动干淋着。我说你这不行,要不你去池塘大叔那儿搓背吧。阿伟就直直地过去了。
阿伟搓背的时候,我先是看见池塘里本来有好几个欢腾着游啊游的,都很快上岸了。
后来搓背大叔也跪了。大叔说娃是十年来一次么,搓的东西今天非把澡堂下水道给堵实了。
那天我们走后,听说他们把池塘换了水。
06
还有次我刚走到宿舍楼道,阿伟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紧接着,对面宿舍的大哥跑了出来。
我说:“这是咋了?”
大哥一边揉眼一边说:“阿伟没带钥匙,就到我们宿舍来呆着。我在上铺睡着呢,忽然就闻到……我一看,阿伟脱了鞋在那看书。这不我就赶快出来了。”
大哥冲进水房往脸上使劲淋水,我说:“阿伟这味是冲了点,但你哭个啥啊?看你眼泪掉的。”
大哥好半天才说:“眼睛被辣到了”。
07
但凡能把生活过成这样,必须是要有点个性的。
阿伟的个性就是特别不善交流,说话非常简短,几乎不说完整句子,都是几个词有节奏感地蹦出。表情也很奇怪,一说话脸就止不住划圆形,和谁说话眼睛不看谁。
大一寒假前阿伟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临潼去,进了几十盒小兵马俑,就是把土烧了后又涂了一层黑漆那种,想要卖给同学。
宿舍6个人给面子,总共买了4盒。身边人卖不掉,阿伟就成天背着,在校园里看见人就卖。
阿伟卖东西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跟在人家后面,忽然拍人肩膀,然后晃着方脸,眼睛盯着别处,用标志性的语气说:“要—不要,兵—马俑”。这事发生在白天,人家好心的以为是搭讪,正常的都分分钟想去报警,更别说是晚上阿伟也这样忽然出现,往往吓得人转身就跑。
结果当然是一个都没再卖掉,校园也隐约流传过“兵马俑怪叔叔”的恐怖故事。
阿伟的第一笔生意就这样失败了。寒假时,他把剩下的几十盒兵马俑都搬上了回家的火车。后来听说当火车到达那个因为高考而被人们熟知的县城时,阿伟的兵马俑早已被颠簸得支离破碎,碎得好像真的是刚出土的一样。
08
关于阿伟的这些囧到离谱的故事,我还有一箩筐。如果有人愿意听,我甚至可以把标题从1写到100。
但在我印象中,阿伟其实也不是完全这么不堪。上天都是公平的,但凡能把生活过成这样,其他方面也一定是要有点天才的。
阿伟的天才,我觉得在于他其实极其聪明,只是被他的外表、气味和说话的方式所掩盖。
阿伟数学尤其好,几乎不怎么听课,做题都不用草稿纸。那些在我看来复杂并难以理解的公式,在阿伟眼里是一种他天生就懂的表达方式——我感觉阿伟对它们有一种天然地理解,他不擅长说话,却似乎能用我们都不懂的语言和它们愉快地交流。
阿伟也不上自习,唯一爱好是窝床上看小说,他还有个奇怪的理论:“知识学会就行了,考试60分就够了。”阿伟最令我们叹为观止的神迹就是大一考了整整11个60分。我问阿伟:“你这么搞,万一不小心挂了怎么办?”阿伟头也不抬,淡淡地说:“不会,都是—算过的。”
阿伟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学习考试,考研也没见复习,一考就刚过线,录取了。后来又读了博,没费啥周折,毕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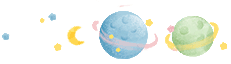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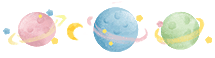
09
激烈的转折发生在大二。
从包容、帮助到产生矛盾,从善意的调侃、偶尔的嘲笑到形同陌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甚至找不到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一切也许源于阿伟的一个不为我们理解的处事方式。
刚开始时是我们对阿伟不爱干净给宿舍环境造成的伤害慢慢失去了耐心,于是开始有了一些争吵。往往有人说阿伟几句,阿伟就蹩脚地反击几句;对方就有点上头,继续数落,阿伟自知嘴笨,就不说话了;对方占了上风,再多说两句,这时,阿伟会做出一个让我们崩溃的举动——他默默地掏出一把钥匙,把抽屉上的锁打开,拿出一个笔记本,把对方很认真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慢慢合上笔记本,放进抽屉,上锁。
我们都跟阿伟吵过,我们都被阿伟记过。
后来马加爵事件发生了。
有一天趁阿伟不在时,我们6个一合计,最少的也应该被阿伟记在本子上4、5次了,这一笔笔、一桩桩,莫不是有朝一日要找我们算账用的。我们心里一阵发毛。
从那以后我们都没再跟阿伟吵过。
阿伟也终于被我们孤立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阿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路人。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我们观察他、提防他,但很少说话。再后来,我干脆搬出去住了。
阿伟上锁的抽屉,诡异的笔记本,一直是我们心里的阴影。
10
后悔之所以让人痛,是因为当你发现当初做了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时,往事已不可重来,过去已再回不去。
我体会到这种痛的时候,离毕业离校已只剩两天了。
阿伟走了。我们没去送他。他走时,早已将课本和那些小说卖给了收废品的,除了几件随身衣服,他什么都没带,脏兮兮的床单和被子散乱在床上,床褥下还压着一双袜子,墙上的美女海报也没撕。
当宿舍还剩3个人时,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撬了阿伟抽屉的锁。
我是最先看那个让我们战战兢兢了两年的笔记本的。出乎我意料的是,笔记本里写的内容远比我想象的多,所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小子果然对我们怨念深重,幸好这两年没出啥事。
然而当我一页页翻看阿伟熟悉的笔迹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前面是阿伟的日记,就是阿伟记下我们的一笔笔、一桩桩,但内容却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有几篇是这样写的:
“贤亮嫌我不洗衣服,我不该顶几句,让贤亮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不敢再说话了,怕贤亮更生气。我会改的,真的很对不起。”
“我真的很讨厌自己,又让朝君生气了,说了要改的怎么又因为懒没改呢,今天记下来,说改就一定要改。”
“朋友们都是为我好,我的独立生活能力真是太差了,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心了。”
后面厚厚的大半本里,短短的记录变成了长篇的文字。在这些字里行间里,我读到阿伟深深的自卑,我读到他无人倾诉的孤独,我读到他对自己的反省和思考,我读到他为了改善表达、交到朋友做出的努力,我读到他的梦想,也读到他暗恋的女生。而且,看到阿伟摘抄了好多《哈佛口才》和《读者文摘》中关于与人相处的内容,我才知道其实他在这两年里,不止看了那几本小说。
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阿伟不止一次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说他很羡慕我把大学生活过得丰富多彩,羡慕我能做许许多多有趣的事,羡慕我有这么多朋友。他说他很想像我一样,很想和我一起去体验大学生活,却不敢告诉我,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后来,当我看到我在学校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小文章,被他小心地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有的还在后面写了自己的文字时,我的眼泪掉下来了。
舍友问:“你看个这个,哭什么?”
我说:“眼睛被辣到了”。
在最后的时刻,我才知道,我们在误解和猜疑中错过了太阳,错过了群星,错过了一个虽然古怪却依然值得珍惜的朋友。
11
再见阿伟又是两年以后了。那时我工作,他读研。
那天我去研究生宿舍找另外一个朋友,路过阿伟宿舍,看他一个人。
阿伟见我的第一句话是:“玩—不玩,魔—方”。
我马上坐到他身边,他递给我一个普通魔方,让我打乱。我认真地扭了好多圈,他拿过去,像机器一样快速翻动,不到半分钟,每个面都恢复了同色。然后,阿伟跟变魔术一样拿出一个我根本没见过的有更多色块的魔方,我扭得杂乱不堪,阿伟又很快地恢复了同色。
叹为观止!
阿伟说:“我—教你,玩—魔方。”
我说“好”。阿伟便一边演示一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计算方法,不厌其烦地讲,根本停不下来。
这是我从叫阿伟“叔叔”以后,他跟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他给我讲的关于玩魔方,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我一直坐在阿伟身边,认真地听了两个小时,直到阿伟说:“明—白了么?”我无比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下午,我心里很舒服,并不是因为我为曾经的误解做了一些弥补,而是我知道了,在阿伟心中,我依然是他的朋友,不,我从来都是他的朋友,虽然我欠他一份尊重。
12
后来,我和阿伟几乎没再见过。阿伟默默地读完博士,悄悄地走了。但每当我回忆大学时光,阿伟便总是第一个从我脑海中冒出来,他奇特的方脸和说话的语气会让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阿伟走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一定会再相见。那时我会给他一个拥抱,我会说:“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13
世界上不会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天上不会有两朵完全相同的云。当一筐鸡蛋抱怨其中的一枚长了毛,也许人家原本就是一颗猕猴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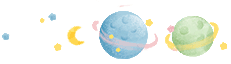
本期主编:王慧敏
责任编辑:吴婷、张振香、王浩洋
执行编辑:于苏静、党文斌

今天点好看,明天变好看
